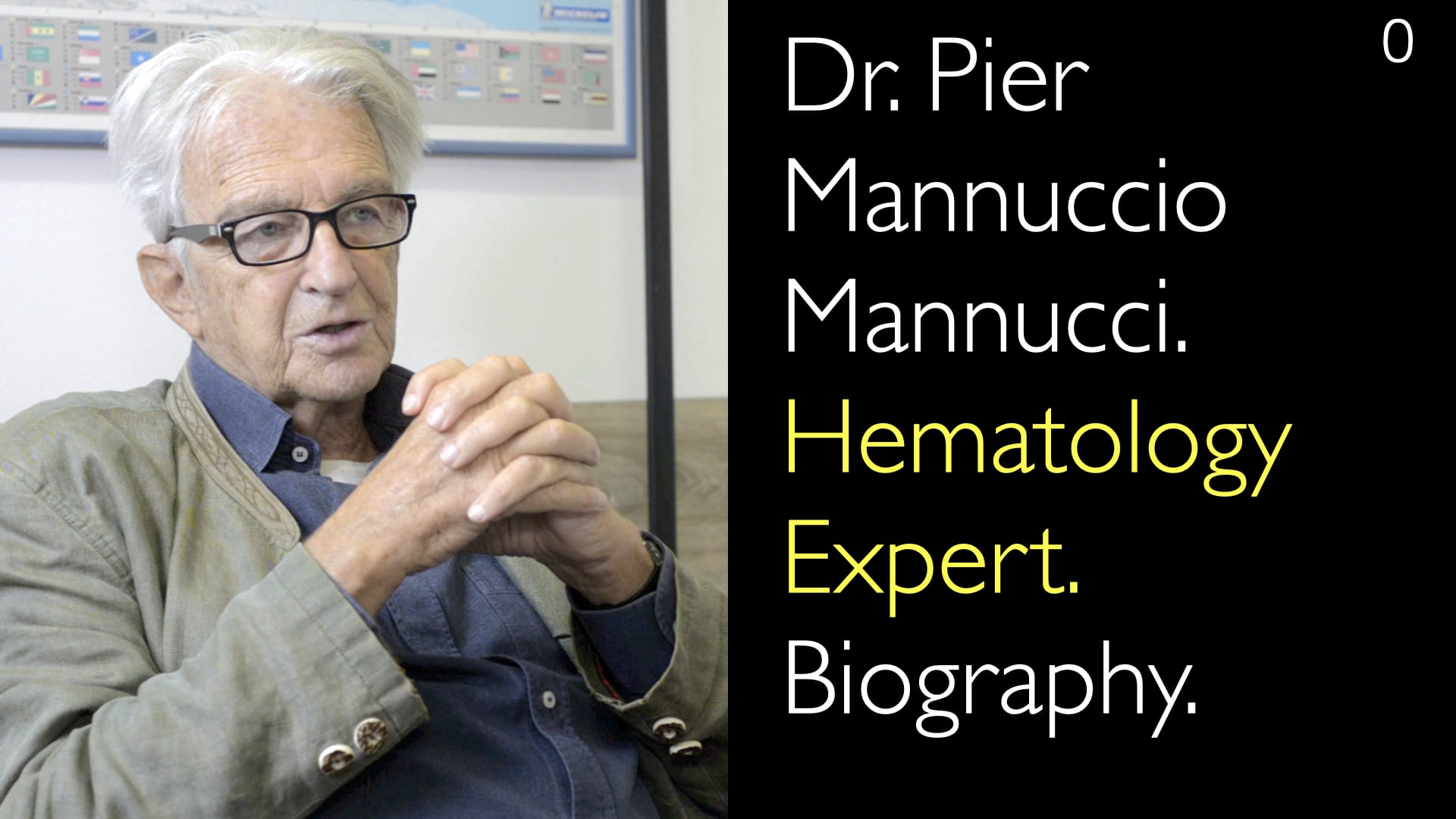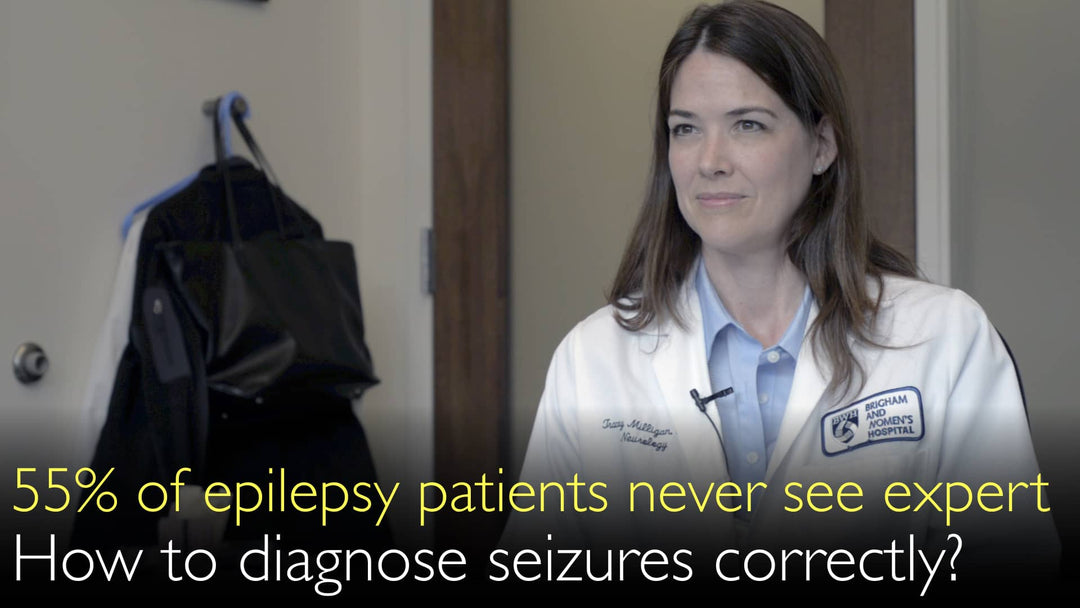空气污染与心血管疾病:机制、风险与预防
快速导航
空气污染如何导致心脏病
细颗粒物(PM2.5)是空气污染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元凶。Pier Mannucci医生解释,这些微粒经肺部吸收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一旦进入血液,PM2.5会激活血小板与凝血系统,形成高凝状态,显著增加动脉粥样硬化血栓事件的风险,包括冠心病和缺血性卒中。
Mannucci医生进一步阐述了第二个关键机制:系统性炎症。暴露于PM2.5会引发轻度但持续的炎症反应,这种慢性炎症直接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与发展。高凝状态与炎症相结合,为动脉血栓形成创造了理想条件。此外,这些颗粒还会损害血管舒张功能,导致血管收缩与高血压。
全球影响与死亡率统计数据
空气污染对全球健康的影响深远且常被低估。Pier Mannucci医生指出,空气污染每年导致近1000万可避免的死亡,占全球年死亡总数6000万的相当大比例。作为死亡风险因素,空气污染仅次于高血压——而它本身正是高血压的诱因之一。
Mannucci医生强调了“人群归因分数”的概念:虽然吸烟对个体的风险更高,但空气污染的暴露范围更广。个人可选择戒烟,却无法停止呼吸。这种普遍性暴露使空气污染成为独特的公共卫生挑战。其影响不仅限于心脑血管与呼吸系统疾病,还包括癌症风险上升,以及新近证实的孕妇早产风险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南更新
鉴于严重的健康威胁,世界卫生组织近期更新了空气质量指南,大幅收紧标准。Pier Mannucci医生指出,PM2.5的安全限值从每立方米10微克降至5微克。这一调整是因为原有标准已不足以保障健康——理论上,安全的污染水平应为零。
新指南揭示了城市人口的严峻处境:即便按旧标准,欧洲也仅有10%的城市区域达标。这意味着高达90%的欧洲城市空气污染处于危险水平。更严格的新标准对政府与市政部门提出更高要求,亟需制定有效政策以减少排放、改善空气质量。
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应对空气污染需先了解其多样化来源,这些来源因地区与季节而异。Pier Mannucci医生指出,除常见的交通污染外,家庭与办公供暖(尤其在寒冷地区)是重要污染源。这一点在COVID-19封锁期间尤为明显:中国北方城市(如北京)的交通减少对空气质量改善有限,因供暖系统仍在运行。
其他重要来源包括农业活动。畜牧业与化肥使用产生的氨气会促进颗粒物形成,自然源(如沙漠尘埃)也有贡献。Mannucci医生将解决方案与气候危机关联,指出化石碳的使用是共同根源。向电动汽车转型、改进建筑保温以减少供暖需求、降低交通总量,是同时应对空气污染与碳排放的关键举措。
个人防护策略
尽管系统性变革至关重要,个人仍可主动减少暴露。在与Anton Titov医生的讨论中,Pier Mannucci医生提供了几条实用且证据支持的建议:最有效的个人防护是贴合良好的FFP2口罩,其过滤细颗粒物的效果远优于外科口罩。他主张在高污染城市中持续使用此类口罩,即使在大流行结束后。
行为调整也能显著降低日常暴露。Mannucci医生建议步行或锻炼时避开单行道与交通繁忙区域,选择公园或绿地等污染较低路线。短途出行选择步行或骑行而非驾车,既能减少个人暴露,也有助于降低社区污染水平。他明确表示,不推荐使用药物(如阿司匹林)对抗污染引发的炎症,因此这些实用避护策略是个人的最佳防御方式。
完整文字记录
Anton Titov医生: 空气污染推升了全球心脏病与肺病的发病率。细颗粒物PM2.5对心肺部疾病的影响比我们先前认知的更为严重。空气污染如何导致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和心律失常?
Pier Mannucci医生: 很高兴您特别关注心血管疾病。空气污染(尤其是细颗粒物或气体)影响呼吸系统较易理解,因为我们每日频繁呼吸。但理解其为何是心血管疾病主因则稍复杂——实际上,它对心脏的影响可能比对呼吸系统更显著。
我将尝试解释这一较新领域的研究。颗粒物,尤其是细颗粒物(直径≤2.5微米的PM2.5及≤0.1微米的超细颗粒),不仅能深入呼吸系统,还可进入血液循环。它们从肺部被吸收入血后,会激活凝血系统,导致高凝状态;同时激活血小板,增加动脉粥样硬化血栓性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动脉疾病与卒中)的风险。
PM2.5还会引发炎症,这是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的另一机制。高凝状态与炎症共同导致动脉系统血栓形成。简言之,PM2.5通过这些途径引发心血管疾病,还包括高血压——它们改变动脉舒张机制,引起血管收缩。此外,PM2.5导致低度系统性炎症,增加癌症风险;新近研究还显示,它会显著提高孕妇早产风险。
空气污染直接或间接造成每年近1000万可避免死亡。全球年死亡人数约6000万,此比例相当可观。空气污染在死亡风险因素中仅次于高血压,而它本身就能诱发高血压。
吸烟与不良饮食也导致死亡,但吸烟可凭个人意志避免,呼吸却无法停止。因此,空气污染虽非头号风险因素,但暴露更普遍。流行病学中,PM2.5具有“最高人群归因分数”:吸烟对个体风险更高,但人群暴露率低。以欧洲为例(其他大陆类似),仅10%的城市区域达到旧版空气质量安全限值——任何超标即对健康有害。
几周前,世卫组织进一步下调了限值。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发现原标准仍不足够。理想安全值应为零,但无法实现;故将PM2.5限值从10微克/立方米降至5微克/立方米。欧洲现需采纳更严标准。美国此前较接近旧标准,但按新指南仍远不足。此标准亦适用于二氧化氮等气体。
面对严峻形势,我们该如何改善空气质量?答案核心是减少污染物,但实施不易。污染源因国而异:交通虽重要,却非唯一来源。供暖(住宅与办公)、沙漠尘埃、农业氨气(来自畜牧与化肥)均为贡献者。
解决方案与气候变化问题同根同源:PM2.5与二氧化碳均源自含碳物质使用。因此,推广电动汽车、改进建筑保温、减少交通量以摆脱化石碳依赖是关键。中国、印度及波兰等地仍高度依赖化石碳。
个人能做什么?虽不能解决全局,但可采取行动。例如,使用FFP2口罩(非外科口罩),因其能有效过滤颗粒物。疫情后我们应继续在街头佩戴它们。其他建议包括:避开单行道(交通更密集)、远离停车场(汽车启动时排放高)、避免在繁忙路段运动、选择公园路线(污染较低)、优化供暖系统。以中国为例:封锁期间,武汉(中南)因交通减少污染下降明显,但北京(北方)因供暖持续,改善有限。这显示供暖与交通同等重要。
米兰与罗马的差异类似(南方供暖需求低),莫斯科等寒冷城市挑战更大。解决需代际努力:年轻一代应对气候危机,也将助力污染控制——英国过去20年污染已减。
回述世卫组织新标准:多数欧洲城市无法达标(仅10%达旧标,90%未达)。他们选择下调限值,因原标准不足且无改善。药物(如阿司匹林)无效对抗污染;请采纳实用建议:戴口罩、避开通勤要道、减少用车。我步行2公里来此即为一例。疫情教会我们:街头行走也应戴FFP2口罩。非人人可迁居清风无交通之地,故此策至关重要。
最后重申:空气污染的人群归因分数高——风险或低于吸烟,但呼吸无法避免,故其影响更广泛。


![空气污染与心脏病:如何降低风险?[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http://diagnosticdetectives.cn/cdn/shop/products/Dr_Pier-Mannuccio_Mannucci_thrombosis_bleeding_hematology_treatment_Diagnostic_Detectives_Network.010.jpg?v=1660905407&width=1080)
![空气污染与心脏病:如何降低风险?[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http://diagnosticdetectives.cn/cdn/shop/products/Dr_Pier-Mannuccio_Mannucci_thrombosis_bleeding_hematology_treatment_Diagnostic_Detectives_Network.010_ec97a2c1-2230-4583-a715-091f7bf9a8e2.jpg?v=1660905418&width=1080)
![空气污染与心脏病:如何降低风险?[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http://diagnosticdetectives.cn/cdn/shop/products/Dr_Pier-Mannuccio_Mannucci_thrombosis_bleeding_hematology_treatment_Diagnostic_Detectives_Network.010.jpg?v=1660905407&width=720)
![空气污染与心脏病:如何降低风险?[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http://diagnosticdetectives.cn/cdn/shop/products/Dr_Pier-Mannuccio_Mannucci_thrombosis_bleeding_hematology_treatment_Diagnostic_Detectives_Network.010_ec97a2c1-2230-4583-a715-091f7bf9a8e2.jpg?v=1660905418&width=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