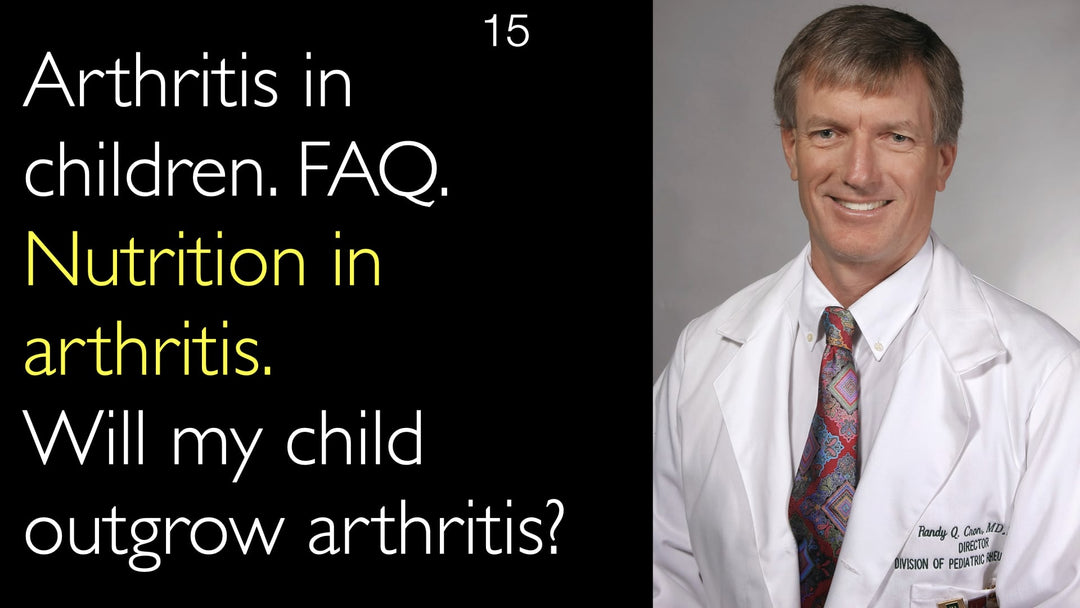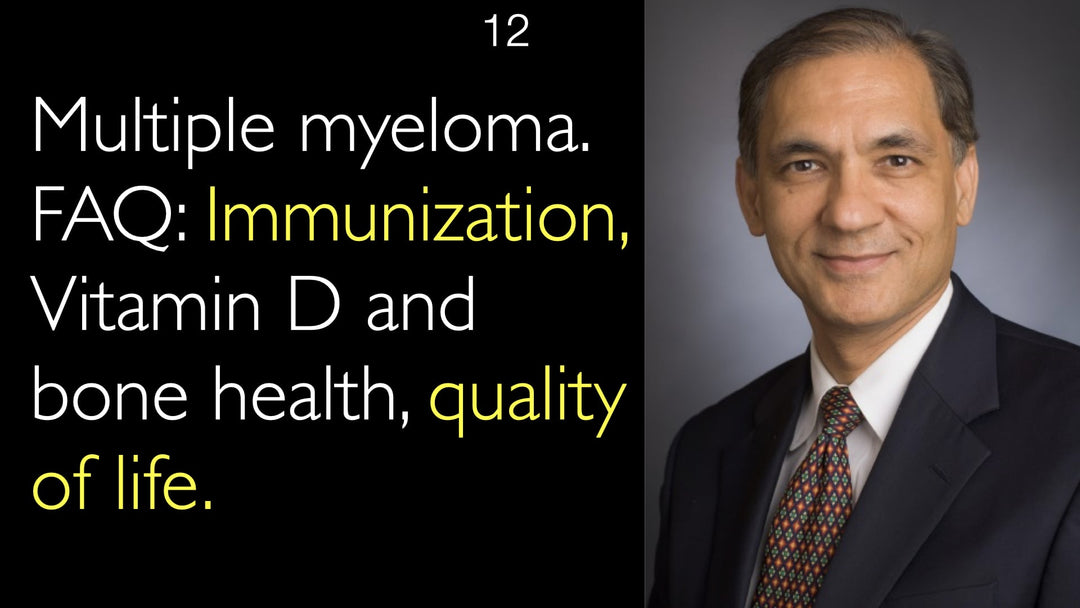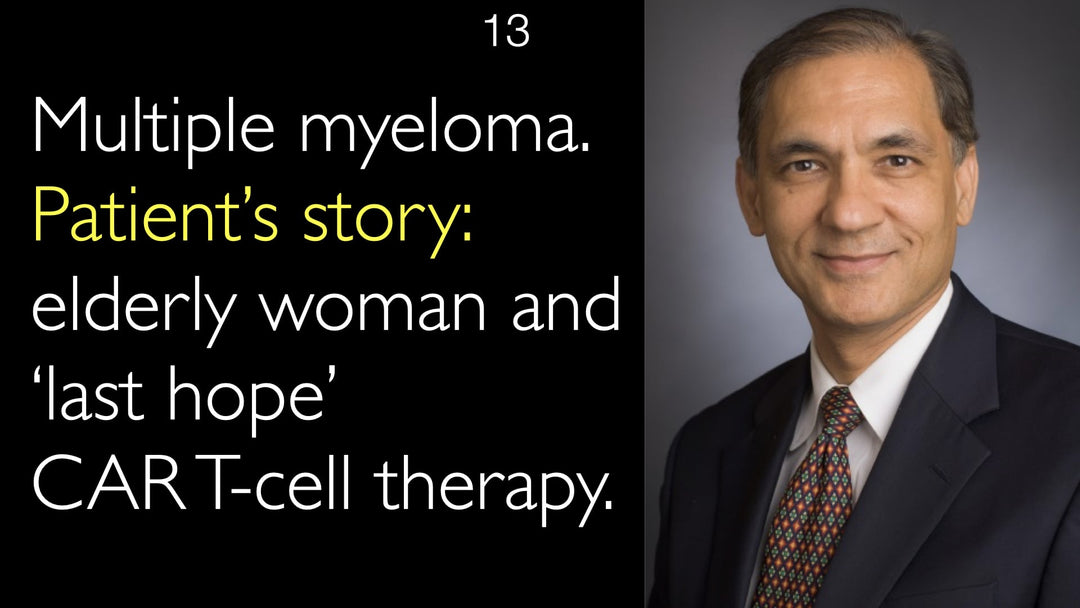本综述深入探讨了儿童炎症性肠病(IBD)患者最佳治疗方案的选择时机与策略。研究表明,克罗恩病早期应用有效的生物制剂可显著改善预后——部分研究显示其缓解率高达85%,而传统治疗仅为60%——但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优势尚不明确。本文还分析了如何识别需强化治疗的患者群体,以及药物使用顺序对长期疗效的影响。
为儿童炎症性肠病选择适时适宜的治疗方案
目录
- 引言:儿童IBD的治疗挑战
- 治疗时机:早期有效干预
- 进展性疾病的治疗策略
- 阶梯治疗的局限性
- 克罗恩病早期治疗的获益
- 溃疡性结肠炎早期治疗的获益
- “早期”定义探讨
- 适宜患者:疾病进程预测
- 影响预后的临床因素
- 临床可用蛋白标志物
- 未来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 适宜药物:治疗顺序与选择
- 一线治疗方案选择
- 治疗顺序的重要性
- 联合治疗策略
- 结论与建议
- 信息来源
引言:儿童IBD的治疗挑战
尽管治疗选择日益丰富,炎症性肠病(IBD)仍面临显著治疗瓶颈。临床试验中,对治疗有反应的患者比例通常不超过30%。许多患者需经历多次药物治疗失败后才能找到合适方案,这一过程可能导致功能障碍、心理压力,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肠壁损伤。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精准医疗——选择适宜的患者、适宜的治疗时机、适宜的药物剂量及监测策略。本文重点探讨如何为适宜患者在最佳时机匹配最佳治疗方案,特别关注儿童IBD领域,该领域相较于成人研究常缺乏特定数据支持。
治疗时机:早期有效干预
治疗启动时机对IBD的有效管理至关重要。当前治疗策略已从传统的“阶梯治疗”(首先使用疗效较弱的药物)转向“早期有效干预”(对适宜患者前期使用强效治疗方案)。
进展性疾病的治疗策略
IBD(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进展性慢性疾病,会导致不可逆的肠壁损伤。现有治疗主要着眼于控制炎症,但无法逆转已形成的肠道损伤。这种自然进展常导致需要手术干预的并发症。
克罗恩病中,纤维化(瘢痕组织形成)是常见并发症,约三分之一患者在不同时期会出现肠道狭窄。儿童期发病的克罗恩病通常比成人期病情更为严重,提示儿童患者更需要早期积极治疗,以预防长期慢性炎症造成的损害。
溃疡性结肠炎直到近年才被确认具有进展性。超过半数患者会出现病变范围扩展,少数会发展为结肠纤维化狭窄。疾病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和活动度都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相关。
阶梯治疗的局限性
历史上,IBD多采用“阶梯治疗”模式,即使对中重度患者,也要求先使用美沙拉秦或硫嘌呤类药物等疗效较弱的方案,失败后才启用生物制剂。现有证据表明,这种方法使患者错过了通过快速控制炎症来改变疾病进程的关键“机会窗口”。
尽管存在这些认识,阶梯治疗仍广泛应用。一项大型美国医保数据库研究(2008-2016年,涵盖28,119名UC患者和16,260名CD患者)显示,仅不到1%的UC患者和不到5%的CD患者接受一线生物制剂治疗。相反,61%的UC患者起始使用5-氨基水杨酸单药治疗,42%的CD患者起始使用皮质类固醇单药治疗。
保险公司常强制要求阶梯治疗,违背医疗建议。2016年克罗恩病与结肠炎基金会的调查发现,40%的患者被保险公司强制要求遵循阶梯治疗,与其医疗提供者的推荐相悖。
克罗恩病早期治疗的获益
多项研究证实了早期有效治疗对克罗恩病的明确益处:
- PRECiSE 2研究:诊断一年内治疗的患者反应率达90%,而诊断五年以上者仅为57%
- CHARM试验:病程短于2年的患者缓解率为43%,2-5年为30%,大于5年为28%
- CALM试验:早期达到深度缓解的患者3年内不良结局减少81%
- VICTORY联盟:病程≤2年的CD患者对维多珠单抗反应更佳
- LOVE-CD研究:早期CD患者(<2年)使用维多珠单抗显示更高的内镜缓解率(45% vs 15%)及联合无类固醇临床与内镜缓解率(47% vs 16%)
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同样支持早期治疗。一项试验将新诊断CD患者随机分配至早期联合治疗(英夫利昔单抗+硫嘌呤)或单用硫嘌呤组。早期英夫利昔单抗治疗使62%的患者在1年时达到临床缓解,而单药组仅为42%。
REACT-1集群随机对照试验(n=1,982)显示,加速阶梯治疗减少了严重并发症及住院或手术需求。
儿童特异性数据强烈支持早期生物制剂治疗:
- RISK队列(n=1,813):早期抗肿瘤坏死因子治疗1年缓解率优于早期免疫调节剂(85.3% vs 60.3%;相对风险:1.41)
- 韩国研究(n=31):诊断后立即使用英夫利昔单抗较常规治疗失败后使用,3年无复发率提高21%
- 欧洲多中心试验(n=100):一线英夫利昔单抗改善10周内镜缓解(59% vs 17%)、52周无需升级治疗的长期缓解(41% vs 15%)及生长结局
溃疡性结肠炎早期治疗的获益
与克罗恩病不同,现有数据并未强力支持溃疡性结肠炎的早期有效治疗:
- Murthy等人研究(n=213):较长病程与较高的1年无类固醇缓解率相关(调整后OR=2.1/10年增加),结肠切除风险更低(调整后HR=0.49/10年增加)
- Mandel等人研究(n=42):诊断3年内早期使用抗肿瘤坏死因子未见获益
- VICTORY联盟:较短病程的UC患者对维多珠单抗反应无改善
- LOVE-UC研究:早期(<4年)与晚期(>4年)UC患者26周缓解率无差异(49% vs 43%)
儿科数据极为有限。一项针对121名UC儿童的研究比较了早期与晚期启用硫唑嘌呤的结局,发现手术率、住院、治疗升级、病变扩展或急性重度结肠炎发作均无差异。
现有文献多为回顾性成人研究,一致显示UC早期治疗无明确获益。欧洲一项活跃的前瞻性试验(SPRINT)正在验证成人UC早期治疗价值,但儿科试验尚待开展。
“早期”定义探讨
对“早期”IBD的定义仍存分歧。有专家建议定为诊断后2年内,但这与其他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常以3个月为界)不同。IBD诊断的长期延迟使定义更复杂,诊断后2年可能相当于发病后5年。
适宜患者:疾病进程预测
为实现精准治疗,明确患者预后至关重要。当前实践结合临床因素与传统实验室标志物,不断进展的研究正在扩展这些预后工具。
影响预后的临床因素
儿科患者中,诊断年龄较小与UC和CD的复发风险增加相关。病变部位/范围也影响结局:
- 克罗恩病:肛周、回结肠和上消化道病变与更严重病程相关
- 溃疡性结肠炎:广泛性结肠炎患者结肠切除风险更高
- 进展性疾病(CD并发症,UC病变扩展)预示不良结局
肠外表现(EIM)和伴随的免疫介导性炎症疾病(IMID)也提示较差预后。一项涵盖93项研究的系统回顾发现,IBD合并其他IMID的患者广泛性结肠炎/全结肠炎风险(RR 1.38)和IBD相关手术风险(RR 1.17)更高。另一项研究显示,既存IMID是不良预后因素(手术风险OR 3.71)。
临床可用蛋白标志物
C反应蛋白(CRP)和粪便钙卫蛋白(FC)是经典IBD标志物。虽主要反映疾病活动度,但也与预后相关:
- CRP升高与CD和UC手术需求增加相关,即使在CD临床缓解期
- 粪便钙卫蛋白在检测肠道炎症方面优于CRP
- 系列FC监测可预测疾病进展/复发
对肠道病原体和自身抗原的血清学反应也具有预测价值:
- 抗酿酒酵母抗体(ASCA)
- 抗鞭毛蛋白抗体(CBir1)
- 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自身抗体
- 核周抗中性粒细胞抗体(pANCA)
一项大型前瞻性儿科CD研究中,更多抗菌抗原阳性与更快进展为复杂疾病相关。高GMCSF自身抗体表达与复杂CD相关,且这些抗体可能在诊断前就已升高。
未来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多个“组学”领域正在开发预测性标志物:
- RISK队列(儿童克罗恩病):识别出预测三年内狭窄风险的细胞外基质转录组特征
- PROTECT队列(儿童溃疡性结肠炎):发现两种预测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的基因特征
- 已验证血液检测:CD8+ T细胞基因表达谱可将患者分为低风险和高风险组(注:类固醇使用可能影响结果)
基因组研究已识别出四个与预后相关的基因位点,这些不同于易感性位点。多基因风险评分和NOD2多态性已被研究,但在RISK队列中,两者均未与儿童CD的狭窄或瘘管形成相关联。
微生物组、代谢组和糖组特征正在开发中以提供预后信息。基于网络的方法可整合多组学数据,助力识别个体化疾病亚型和最优治疗方案。
适宜药物:治疗顺序与选择
历史上因缺乏头对头比较试验,一线治疗决策难以基于数据,但这一状况正在改变。
一线治疗方案选择
近期头对头试验提供了宝贵比较数据:
- VARSITY试验(n=769名UC患者):维多珠单抗1年结局优于阿达木单抗(临床缓解率:39% vs 23%;内镜改善率:40% vs 28%)
- SEAVUE试验(n=386名CD患者):乌司奴单抗与阿达木单抗无显著差异,但前者内镜应答有改善趋势
- 其他近期试验:依洛珠单抗与英夫利西单抗无显著差异,阿达木单抗与对照药物亦无显著差异
- 古塞奇尤单抗 vs 乌司奴单抗:IL-23抑制剂与IL-12/23抑制剂比较无显著差异,可能因统计效力不足
治疗顺序的重要性
随着新疗法不断涌现,理解治疗顺序的影响日益重要。一线治疗反应率仍相对较低——约三分之一患者在随访期间持续使用首种生物制剂,三分之二需更换疗法。
多数新疗法数据来自抗肿瘤坏死因子(抗TNF)治疗失败后的研究。二线及后续疗法通常疗效递减,突显了一线选择的重要性。
抗TNF失败后使用维多珠单抗和乌司奴单抗的研究结果不一:
- 两项研究支持抗TNF失败后乌司奴单抗优于维多珠单抗
- 一项研究显示抗TNF治疗后序贯使用维多珠单抗或乌司奴单抗作为三线治疗无显著差异
抗IL23药物(瑞莎珠单抗、米利珠单抗、古塞奇尤单抗)在既往生物制剂失败后可能不降低疗效。抗TNF无应答者显示IL23p19、IL23R和IL17A上调,为这些现象提供了生物学解释。
与晚期CD相比,早期CD患儿显示更高的IL12p40和IL12Rb2信使RNA水平及T细胞产生的干扰素-γ,提示IL-12可能是早期疾病和抗TNF难治性疾病的重要通路。
JAK抑制剂(托法替尼、乌帕替尼)在生物制剂失败后仍保持疗效,可能因其清除机制不同于生物疗法。然而,其他小分子药物(S1P受体调节剂)在多次生物制剂失败后表现不佳。
联合治疗策略
合理早期联合治疗可能通过靶向互补生物学通路提高应答和缓解率。SONIC研究著名地证实了硫嘌呤+抗TNF联合疗法的优越性,但随着优化单药治疗可避免硫嘌呤不良反应,该策略已较少使用。
存在成人和儿童其他联合方案的观察性数据。VEGA试验(n=214)比较了戈利木单抗+古塞奇尤单抗联合与单药治疗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的效果。联合治疗更易实现内镜改善,且不良事件未增加。EXPLORER研究探讨了维多珠单抗+阿达木单抗+甲氨蝶呤联合方案。
结论与建议
证据强烈支持儿童克罗恩病的早期有效治疗,多项研究显示显著改善的结局,包括更高缓解率(85.3% vs 常规治疗60.3%)、更好生长和减少并发症。对于溃疡性结肠炎,获益似乎较不明确,数据未能强力支持早期积极治疗。
预测需早期积极治疗的患者需评估临床因素(诊断年龄、病变部位、肠外表现)和可用生物标志物(C反应蛋白、粪便钙卫蛋白、血清学标志物)。新兴组学技术有望提升预后能力。
治疗顺序至关重要,一线选择尤为关键,因后续疗法常疗效递减。头对头试验正为这些决策提供更多数据,但仍需更多儿科特异性研究。
对于面临儿童IBD治疗决策的家庭,本研究强调:
- 早期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至关重要
- 克罗恩病常受益于更早的生物制剂治疗
- 保险障碍仍是获得适当治疗的重要挑战
- 治疗顺序决策应考虑长期结局
- 持续监测和调整治疗必不可少
信息来源
原文:《为儿童炎症性肠病选择正确时机的正确治疗:顺序是否重要》Elizabeth A. Spencer, MD, MSc
出版物:《北美胃肠病学诊所》第52卷,2023年,517-534页
注:本文基于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在保持原科学出版物完整内容和数据的同时,以患者友好型方式呈现,便于炎症性肠病患者及家庭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