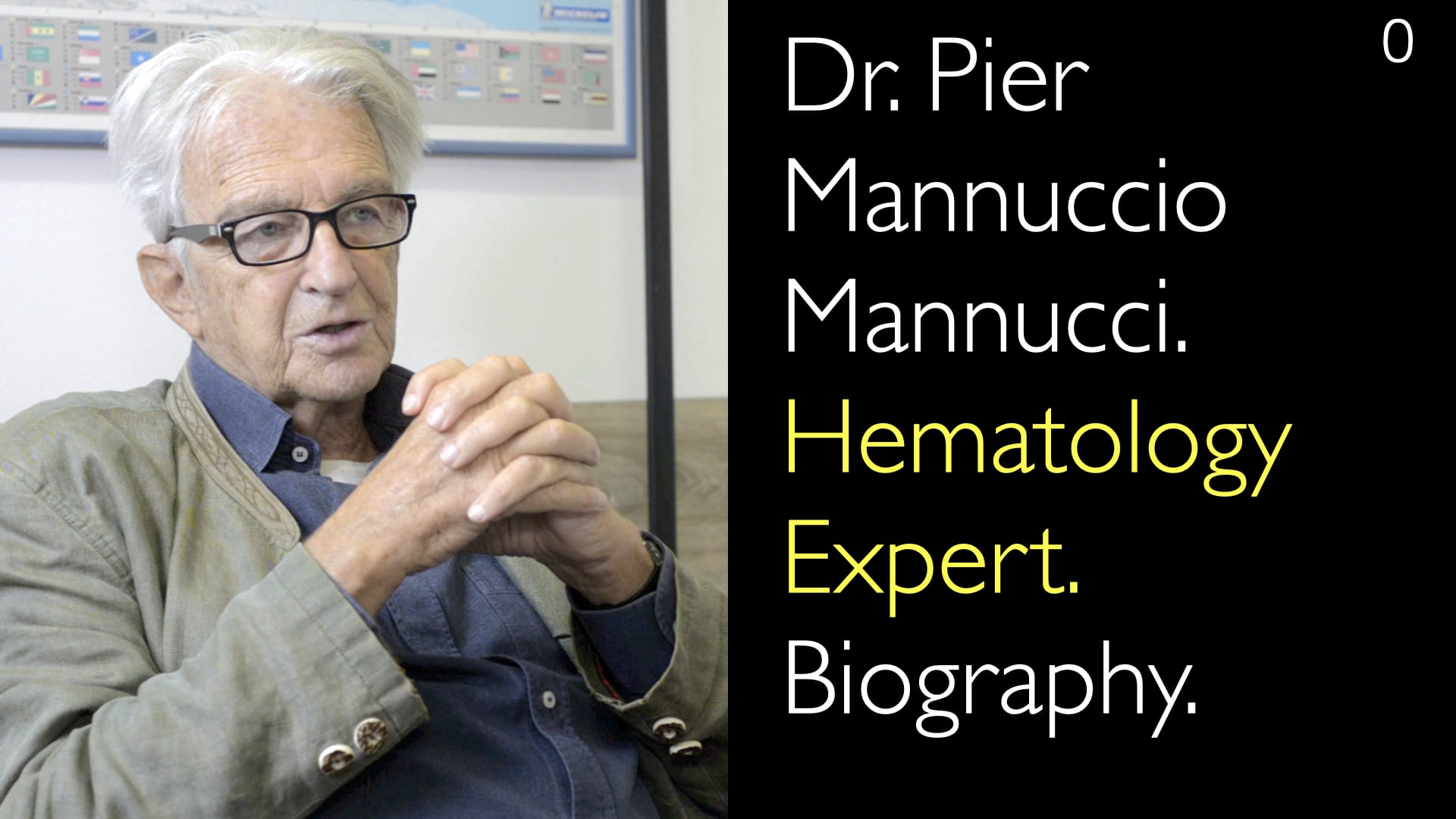遗传检测评估血栓风险:何时真正有价值?
跳转至章节
常见易栓症突变解析
医学博士Pier Mannucci医生阐述了与静脉血栓形成风险增加相关的最常见基因突变。这些属于凝血因子的功能获得性突变。因子V莱顿突变导致因子VIII过度活跃,引发凝血功能亢进。凝血酶原基因突变则造成凝血酶(凝血级联反应的终末酶)过量生成。
Mannucci医生强调了一个关键区别:这些突变是风险因素,而非疾病的必然保证。它们会增加相对风险,但对大多数携带者而言,血栓事件的绝对风险仍然较低。他指出这些突变相当常见,在西方国家普通人群中的携带率约为6%。
筛查建议与指南
医学博士Pier Mannucci医生明确了不推荐进行基因检测的情形。无需对健康人群进行普遍筛查。对于面临暂时高风险情况的人群(如髋关节置换等大手术),也不建议进行检测。
他特别提到一种常见转诊情况:妇科医生有时会要求对年轻女性在开具雌激素-孕激素复合避孕药前进行检测。Mannucci医生指出,指南并不支持这种做法。突变风险过于罕见,不足以证明普遍筛查的合理性。对于突变携带者而言,妊娠本身的血栓风险与避孕药风险相当。
检测结果的临床价值
反对常规检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对患者治疗缺乏实际影响。Mannucci医生解释称,在发生血栓后发现易栓症突变并不会改变治疗方案。无论患者的基因状况如何,抗凝治疗的持续时间都保持不变。
检测的主要价值通常在于心理层面,能为血栓事件(尤其是年轻患者)解答"为何发生"的疑问。但Mannucci医生提醒,阴性检测结果并不能排除其他病因。很多时候找不到单一原因。他的结论是:这些检测对于指导治疗或预测未来风险"相当有限"。
无症状人群基因检测的风险
医学博士Pier Mannucci医生强调了针对无症状个体进行检测的重大弊端。阳性结果会打上"遗传特质标签",引发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惧。这对儿童尤为值得关注,因为检测会给他们贴上非疾病的健康标签。
他引用了一项针对百岁老人的研究数据:这些突变的流行率为6%,与普通人群完全一致。这证明携带者完全可以享有健康长寿的人生。这些突变甚至可能在历史上具有生存优势——通过减少分娩或创伤时的致命性出血。
Mannucci医生还警告了意外的家族发现:若患者父母检测为突变阴性而患者为阳性,可能引发关于亲子关系的难题。这揭示了在没有明确医疗指征时追求基因信息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
高风险情境的实用建议
医学博士Pier Mannucci医生提供了管理血栓风险的实用指导。他以具有多重风险因素的长途飞行为例,明确反对使用低分子肝素或阿司匹林等预防性药物。
相反,Mannucci医生主张采取非药物措施:通过饮水保持水分、避免酒精和含糖饮料、定期在机舱行走防止静止不动。他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风险意识才是最佳防御策略,而非抢先药物干预。正如医学博士Anton Titov在讨论中指出的,这种方法与国际文献和专家共识一致。
完整文字记录
医学博士Anton Titov: 腿部静脉血栓和盆腔静脉血栓可能导致肺栓塞。血栓常发生于存在多种基因突变的人群,如蛋白C、蛋白S或抗凝血酶基因。血型也会影响血栓形成倾向。人们通常如何发现自身存在导致血栓形成的基因突变?
医学博士Pier Mannucci: 这是个漫长的故事,我曾参与其中,因为多年前我是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凝血因子功能重要突变的规模让我们认识到高凝状态的存在。我们部分解释了这些现象——发现了一些(虽非全部)静脉血栓(而非动脉血栓)的成因。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突变发生频率很高,因此在普通人群中具有相关性。我们主要处理功能获得性突变。一种血栓风险突变称为因子V莱顿。如我所述,因子V莱顿突变会产生高度活跃的因子V,这自然导致过度凝血,增加血栓形成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因子V莱顿突变风险因素并不意味着必然患上血栓疾病。它只表示你比无突变者面临更高风险。但我们必须区分相对风险与绝对风险——即便对这些患者而言,绝对风险仍然很低。
另一种已确认的功能获得性突变存在于凝血酶原中。这里同样会出现凝血酶(凝血过程的最终酶)的过量生成。这是同样重要的发现,虽未获诺贝尔奖,但在我们领域无疑是基础性发现。
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些突变。若将这两种突变合并计算,它们在普通人群中非常常见。在西方国家普通人群中,因子V莱顿和凝血酶原突变合计达6%。因此携带这两种突变的概率相对较高。但再次强调,这些只是血栓风险因素,并非必然发病的指征。
医学博士Anton Titov: 目前对因子V莱顿和凝血酶原突变有哪些建议?何时应对患者进行这些突变检测?
医学博士Pier Mannucci: 显然不需要对普通健康人群进行检测。甚至对接受具有附加血栓风险操作(如手术,特别是髋关节置换术)的人群,或服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也无必要。因为尽管这两种风险因素具有叠加(甚至倍增)效应,但突变发生率太低,不足以支持进行此类筛查。
例如最常见的转诊情况:妇科医生有时要求对服用雌激素-孕激素复合避孕药的年轻女性进行突变分析。我们通常不建议进行血栓相关突变检测——基于我提到的原因,这已写入指南。这些检测效用甚微,因为许多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并未发生血栓。
还需考虑:若不服药,她们可能会怀孕。而妊娠本身携带的血栓风险与避孕药及血栓易感突变的风险相当。因此通常不建议对因子V莱顿、蛋白C和蛋白S突变进行筛查——不仅针对普通人群,甚至包括口服避孕药或高风险手术前的情形。故不推荐筛查。
如我所说,这些检测通常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旨在理解血栓成因。对血栓易感突变的筛查尤其多见于年轻人。因为如您所知,静脉和动脉血栓都是与年龄相关的病症。
举例说明:育龄女性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几率是万分之一(截至40-45岁)。但女性绝经后风险变为千分之一,60-70岁以上时更高达百分之一。
计算表明:对普通人群进行血栓易感突变筛查并不值得。但您会问为什么?事实证明:假设我发生血栓后想了解成因,除了其他风险因素外,我检测了因子V莱顿、蛋白C或蛋白S突变。
但获得这些信息后能做什么?我只是了解到血栓的某个可能风险因素。这会影响未来治疗或行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治疗方案不会改变:对发生血栓的患者治疗周期将根据其他状况确定,与其是否携带易栓突变无关。
血栓易感突变信息也不影响抗凝治疗时长。换言之,不会因存在这种增加血栓风险的突变而延长治疗。总而言之,普遍建议不开展这些研究,因为它们既不能帮助预防血栓,也无法为已发病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它们仅有助于理解血栓成因。但通常突变只是血栓的多个风险因素之一。有时即使患者突变检测阴性,也找不到血栓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血栓易感突变曾引发高度关注——它们确实极大丰富了我们的认知,但实际应用有限。
我们理解了凝血因子功能获得与功能丧失在凝血障碍中的重要性对比。正因如此,这个课题由像我们这样既处理出血性凝血问题、也处理过度凝血(即血栓形成)的专家来探讨。但易栓性突变实际临床价值甚微,尽管它们是非常有趣的突变。
第五因子莱顿突变、蛋白C或蛋白S突变可能相对良性。这类易栓性突变在普通人群中极为常见。或许在人类早期,携带这些突变者具有生存优势——原始人与野兽搏斗时伤口不易出血,突变可能帮助其更易止血。
这就是此类突变能持续遗传的原因:它们曾是优势突变。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女性而言,这种突变在分娩早期尤其有利。当时许多女性因分娩出血死亡,而易栓性突变能降低出血风险,故得以遗传。直到近现代,血栓发生频率才显著增加。
但在我看来,这些突变既未改变静脉血栓栓塞的自然病程,也未影响其治疗方案。这就是我的核心观点:这些突变非常有趣,我们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可见我的文献目录),但我的观点符合学界共识。
目前第五因子莱顿、蛋白C或蛋白S突变检测开展频繁,主要源于临床需求——以我的经验,特别是年轻血栓患者发病时不符合其年龄特征。医生希望探究病因,患者最常问的是"我为何会得血栓?"而非"未来会如何发展?"
这就是易栓性突变检测有时被实施的原因。但我认为其实际效用有限。
对于无症状个体,即使通过日益普及的基因筛查发现携带蛋白相关突变(如第五因子莱顿、蛋白C或蛋白S突变),也缺乏有效干预手段。我不建议无指征的基因筛查——首先结果解读存在困难,且如我所言:这些突变只是血栓形成的辅助因素,不能作为禁孕或禁用口服避孕药的依据。
我们在米兰对百岁老人的研究发现:这群健康长寿者中易栓性突变携带率达6%,与普通人群无异。这意味着携带者同样可享百岁高寿,突变并非致命因素。因此我本人不会进行前述突变筛查。
尤其当患者因血栓事件接受检测后,常会追问:"我的孩子是否遗传了突变?"这时问题更复杂——若父母双方均无症状却检出突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例如父子关系质疑)。对于五岁幼童,更不应贸然进行基因标记:即使解释这是遗传特征而非疾病,负面标签效应仍不可小觑。
最近有瑞士公司拟开发针对口服避孕药女性的基因检测系统,虽包含多功能获得性突变检测并生成血栓风险评分,我仍持保留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某些检测试剂盒包含未获证实的血栓相关突变位点,我的诊所就接诊过此类检测结果咨询者——他们携带的杂合/纯合突变其实与血栓无关。
需要明确:第五因子莱顿、蛋白C或蛋白S突变是明确的风险因素,但非血栓形成的直接病因。
医学博士Anton Titov: 假设一名40多岁男性因工作需频繁乘坐8-12小时国际航班,基因检测发现第五因子莱顿突变,同时携带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注意:这不意味着患病)。查阅十年体检报告发现其红细胞计数持续高于正常上限,红细胞压积始终>50%。此时他该如何决策:长途飞行时是否需注射低分子肝素?或忽略检测结果?
他的血型是A型还是B型?
医学博士Anton Titov: 血型如何影响血栓风险?您对此类案例有何建议?
医学博士Pier Mannucci: 首先我根本不会建议进行这些检测。即便存在多重风险因素,我的做法是:不使用肝素或阿司匹林预防;飞行中限制饮酒,多饮无糖无酒精饮料(最好是水);保持活动避免久坐,经常起身行走。目前没有任何指南推荐长途飞行前预防性注射低分子肝素——荷兰Frits Rosendaal博士的临床研究也支持该观点。当然,不能否认媒体报道的极端案例(如服用避孕药的女护士在24小时航班后因肺栓塞死亡),但这不能成为实施可能有害的预防治疗的理由。
"药物"在希腊语中既指良药也指毒药——正如我们将讨论的多药治疗问题。我的建议是:无需采取任何药物干预,通过健康生活方式(适度运动避免淤滞)管理风险。即便我本人(早期研究中曾作为志愿者参与实验室方法开发)未携带易栓突变,我也会给出相同建议。这与文献推荐一致,其他专家在此问题上观点也应相似——虽不愿武断,但我相信共识如此。


![血栓风险与基因突变:是否需要进行基因检测?
4. [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http://diagnosticdetectives.cn/cdn/shop/products/Dr_Pier-Mannuccio_Mannucci_thrombosis_bleeding_hematology_treatment_Diagnostic_Detectives_Network.005.jpg?v=1660905312&width=1080)
![血栓风险与基因突变:是否需要进行基因检测?
4. [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http://diagnosticdetectives.cn/cdn/shop/products/Dr_Pier-Mannuccio_Mannucci_thrombosis_bleeding_hematology_treatment_Diagnostic_Detectives_Network.005_a2c60dd0-4ea9-4383-ae40-4f9644026086.jpg?v=1660905322&width=1080)
![血栓风险与基因突变:是否需要进行基因检测?
4. [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http://diagnosticdetectives.cn/cdn/shop/products/Dr_Pier-Mannuccio_Mannucci_thrombosis_bleeding_hematology_treatment_Diagnostic_Detectives_Network.005.jpg?v=1660905312&width=720)
![血栓风险与基因突变:是否需要进行基因检测?
4. [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http://diagnosticdetectives.cn/cdn/shop/products/Dr_Pier-Mannuccio_Mannucci_thrombosis_bleeding_hematology_treatment_Diagnostic_Detectives_Network.005_a2c60dd0-4ea9-4383-ae40-4f9644026086.jpg?v=1660905322&width=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