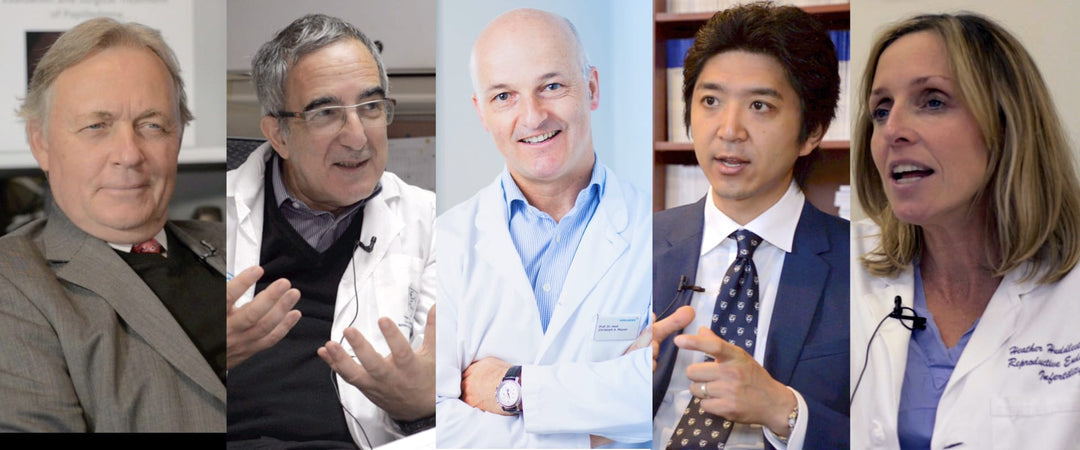安东·季托夫医学博士对上述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雷帕霉素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潜力疗法的突破与障碍
跳转至章节
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在衰老生物学领域的困境
Matt Kaeberlein博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指出,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存在根本性缺陷。他强调,生物衰老是该疾病的最大风险因素,但研究界普遍忽视了这一关键联系。在与Anton Titov博士(医学博士)的讨论中,Kaeberlein医生将这种疏忽称为“令人难堪”。
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超过一半的预算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但仅有少量资金用于探索衰老的生物学基础。Kaeberlein医生认为这种资源分配是重大的战略失误。最近获批的靶向β淀粉样蛋白药物对患者无实际益处,进一步凸显了当前研究方向的局限性。
雷帕霉素临床试验的紧迫性
Matt Kaeberlein博士强调,雷帕霉素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试验本应在十五年前启动。他对研究界和临床领域的不作为深感失望,并认为这些领域因未在痴呆症背景下测试雷帕霉素而“应当感到羞愧”。
在与Anton Titov博士的对话中,Kaeberlein医生指出,雷帕霉素在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中已显示出显著疗效,具有延缓甚至预防痴呆进展的潜力。尽管临床前证据充分,人体试验仍严重滞后。
仿制药资金筹措的挑战
雷帕霉素作为仿制药,面临临床试验资金不足的难题。Matt Kaeberlein博士承认,制药公司缺乏开发仿制药的经济动力,导致相关研究进展缓慢。
Anton Titov博士以阿司匹林等通用预防药物为例,指出这些药物虽具显著健康益处,却因仿制药身份难以获得充足研究资金。尽管全球政府承担着阿尔茨海默病护理的巨大成本,公共卫生机构仍未优先考虑雷帕霉素试验,尽管其长期可能带来显著节约。
雷帕霉素的声誉困境
Matt Kaeberlein博士认为,声誉问题是雷帕霉素研究的主要障碍。该药物因在器官移植患者中作为免疫抑制剂而闻名,高剂量使用时曾出现多种副作用。
这一历史背景导致医生群体中形成了持久的负面认知。许多临床医生仍持过时的安全性观点,未充分考虑更新的给药方案。Kaeberlein医生在与Titov博士的访谈中详细解释了这一挑战。
副作用的误解与澄清
Matt Kaeberlein博士澄清了关于雷帕霉素副作用的常见误解。数据显示,低剂量间歇使用风险极低,在健康人群中每周服用低剂量时,副作用轻微,常与安慰剂无异。
他强调,移植患者的经验不能反映雷帕霉素在预防背景下的安全性。即便存在更明显的副作用,延缓阿尔茨海默病发病10-15年的潜在益处也足以证明其合理性。然而,这一观点在临床讨论中仍常被忽视。
临床认知的转变
Matt Kaeberlein博士对改变临床认知持谨慎乐观态度。他注意到,不同疾病领域对细胞衰老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标志着医学界正逐渐认识到衰老生物学在年龄相关疾病中的作用。
他承认,改变医学观点需要大量时间和证据,并在与Titov博士的讨论中表达了时而沮丧、时而乐观的心情。他相信,评估雷帕霉素在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年龄相关疾病潜力的势头正在形成。
完整文字记录
Anton Titov博士(医学博士): 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数十亿美元被投入失败的药物研发,这些资源本可重新定向至衰老研究——考虑到其惨淡的成果记录。而雷帕霉素,正如您在同行评审文章中所写,也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现在是否是开展雷帕霉素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试验的时机?
Matt Kaeberlein博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 是的,雷帕霉素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试验在十五年前我首次提议时就该进行。说我对阿尔茨海默病领域忽视衰老生物学——尤其是对雷帕霉素的忽视——不感到沮丧,那是轻描淡写。我认为他们应当感到羞愧。
雷帕霉素至今未在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痴呆症背景下进行测试是毫无借口的。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界的失败,在我看来也是临床界的失败。
因此,我认为这方面潜力巨大。但退一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这并非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界独有,但在该背景下尤为突出——我们知道生物衰老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大风险因素。这一点非常明确。
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界未关注这一联系,在我看来是令人难堪的。目前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过半预算仍专门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却未考虑生物衰老在其中的作用。
仅少部分预算用于理解衰老生物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任何关注此事的人都应清楚这一直是个错误。
我认为目前获批的靶向β淀粉样蛋白却对患者无益的药物,也应当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将所有研究精力集中于β淀粉样蛋白而非研究导致阿尔茨海默病易感生理机制(即生物衰老过程)是重大失误。
我当然希望这种情况能改变。生物医学领域的范式转变需要很长时间。但我感觉这种转变正在开始发生。
我感到人们开始理解衰老生物学机制与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年龄相关疾病的关联。例如,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界、肥胖领域和癌症领域对衰老细胞研究的增长表明,生物医学界终于开始关注我们多年来的主张。
即这些生物衰老标志确实为年龄相关疾病创造了易感环境,并可能在其中起因果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只要我们理解这种生物学机制,是否因果相关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在人们患病前进行干预,防止他们发生阿尔茨海默病或年龄相关癌症、肾脏疾病、心脏病及免疫衰老。
是的,所有这些疾病的共同点就是生物年龄是最大风险因素。所以,是的,令人沮丧,但也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感到乐观。我希望这种趋势能持续。
Anton Titov博士(医学博士): 您认为这是否有些争议?我在伦敦与一位著名数学家交谈过,他在确定他莫昔芬对乳腺癌的预防作用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Jack Cuzick医生——他表示阿司匹林是戒烟后预防癌症的第二重要措施。显然相关研究很多,但阿司匹林是仿制药,因此制药行业无法从广泛可及的仿制药中赚取数十亿美元也是部分原因。
所以进行昂贵临床试验的动力较小。雷帕霉素是仿制药。您认为这是否与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痴呆症中雷帕霉素临床试验缺乏主要资金支持有关?尽管这些试验不一定由制药界资助,而是由公共卫生机构支持。毕竟,全球政府承担着阿尔茨海默病护理的巨大成本,这不只是制药行业的事。
Matt Kaeberlein博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 是的,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这是部分原因。虽然不认为这是主要挑战,但毫无疑问,开发雷帕霉素缺乏经济利润激励确实导致了进展缓慢。
但实际上更大的问题是声誉问题。这源于雷帕霉素最初用于器官移植患者并获得FDA批准。因此它获得了免疫抑制剂的名声,在该患者群体中会产生一系列不算严重但也不理想的副作用。
在器官移植患者每日高剂量使用时,至少有相当多的副作用与雷帕霉素相关。因此在临床界,由于其开发和使用方式,许多医生形成了雷帕霉素副作用严重的认知。
在我看来数据很明确。我认为大多数阅读过低剂量每周一次雷帕霉素用于健康人群研究的人都会同意:在这种背景下,雷帕霉素的副作用非常小。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安慰剂无异。
但由于声誉已经形成,我发现在临床界克服声誉问题十分困难。因此我认为缺乏利润动机和——可能更重要的——雷帕霉素面临的声誉挑战共同构成了制药界之外资助临床试验的障碍。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可以告诉您——因为我曾与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及其他可能资助此类研究的团体交流过——当你向他们展示数据,证明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所有小鼠模型以及痴呆症和帕金森病的小鼠正常衰老研究中,雷帕霉素都有效且效果显著时,
他们会对开展临床试验充满热情。但随后他们会咨询某些对数据一无所知、可能从未使用过雷帕霉素的医生,却被告知该药物存在诸多副作用。而当他们的专家表示“雷帕霉素确实有很多副作用”时,他们对研究其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兴趣就会减弱。
因此我认为这一直是个问题。我同样难以理解的是,即便雷帕霉素的副作用与此情境下器官移植患者所见的副作用相当,如果我有一位亲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我确信他们和我都愿意承受这种程度的副作用——前提是能够将阿尔茨海默病延缓十年、十五年,甚至可能完全预防。
所以我至今仍不完全理解对副作用的担忧。更何况这种担忧并不符合事实。我认为这十分令人遗憾。所幸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
我的情绪常在挫败与乐观间徘徊:挫败于进程缓慢,乐观于终于感受到势头——人们开始实际收集副作用与风险数据,并逐步改变临床界对雷帕霉素的认知。前路依然漫长,但我认为这确实是阻碍此类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临床试验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